我的“豆腐年” | 德州云-德州晚报全媒体
作者 春仲
记得小时候,过年时家里都是买上几斤豆腐,但有一年却是破天荒地去豆腐坊做了一个豆腐。
那年好像是我刚上初中,已经放寒假了,头天下午母亲对我说:“赶明儿你去二姨家那里做一个豆腐吧,豆子我都泡上了,我明早儿上给你准备出来,豆腐坊那边都说好了。推个小车去,别骑车子,回来推着稳当。”
第二天上午,吃过早饭,我就推上小推车,拿上泡好的豆子去了离我们村5华里的二姨家,在姨家二哥的陪同下去了豆腐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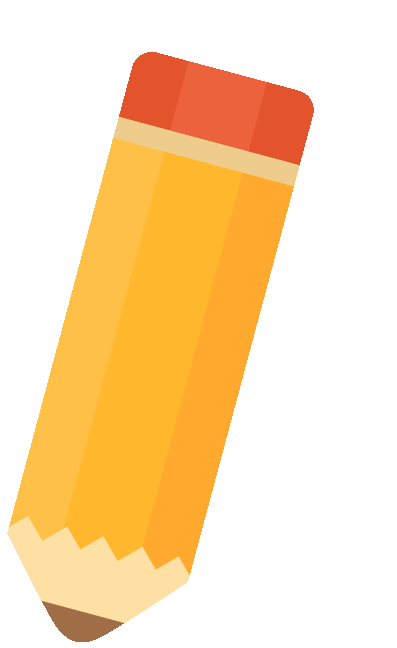
豆腐坊就在一户人家专门辟出来的一间北房里。我们去的时候,院子里两条并摆着的板凳上放着一个木盒子,木盒子上面有一块石头,压着木板下面用白布包裹起来的豆腐,沥出的水一滴滴滴在下面的土地上,有的已结成了冰,豆腐盒子还在微微冒着热气。看来,这是今天做好的第一个豆腐。进了房门,右侧是一个熬豆浆的大锅头,往里去西边靠墙是一个专门磨豆浆的石磨,靠东墙是高高吊在屋顶上的一个过滤豆浆的白布包。大锅里正熬着豆浆,好像是生豆浆刚倒进锅里,上面泛着白泡。
见我们进来后,有人热情地打着招呼,问我:“你是‘寺上’(我村村名)的吧?”我笑着点点头,那人目光一转,对着姨家二哥说:“来,咱们先磨豆子,这一锅一会儿就好了,磨好豆浆就做咱们这个。”他一边说一边就把我手中的豆子接过去,倒在石磨旁边桌子上的瓷盆子里,又对二哥说:“你和你这个兄弟摇磨子,我来续豆子。”圆形的石磨直径大约有六七十公分,分上下两片,下片厚一些,是固定不动的;上片薄一点,是可以通过手中的“摇杆”推动其转动的。石磨转动的同时,那人搲了一勺豆子倒进磨眼里,接着又舀了一瓢水,这时顺着石磨就有白色的豆浆开始流下来了,沿着浆槽,流进了下面的铁桶里。一边干着,那人一边说:“咱这里做豆腐的水都是从北边运河里挑过来的,水好,豆腐也好吃。这水加少了不行,加多了也不行,跟挤出来的羊奶差不多稠就行。”干着,说着,很快豆浆就磨完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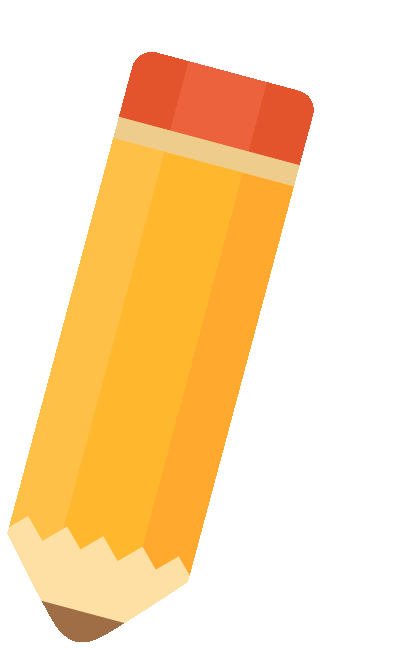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,只见旁边的大锅里豆浆已沸腾起来了,有人用一个长长的大勺子,搅动几下再把豆浆撩起来倒下去,好像是“扬汤止沸”。看样子,这人是豆腐坊的师傅。掌勺师傅看我们这边也磨完了,回过头来对我们说:“你们赶紧把浆滤出来吧,这一锅马上就好了。”和我们一块磨浆的那人一边嘴上应着“好来”,一边手脚麻利地把浆桶提过去放在了过滤包旁边,回头对二哥说:“来帮一下,我把豆浆倒进去。”我这才注意到,过滤包固定在一个钢筋做成的方框上,四个对角也用钢筋连成了一个十字,十字中间拴了一根粗麻绳,吊在了屋顶的檩条上。过滤包是一块方形的白布,四个角栓绑固定在方框的四个角上。包的下面放了一个大盆。原浆倒进包里后,那人不断地上下抖动翻滚着包里的豆浆,过滤后的豆浆就“哗哗”流进了下面的大盆里。最后剩在包里的豆渣,那人先是和二哥用两根木棒夹住变换不同的位置挤压,挤压一遍后加上点水又挤压一遍,渣团越来越小了又用手挤压,最后实在挤不出豆浆来了才肯罢休。
这边豆浆过滤好了,那边的锅也刷干净了,那人端起瓷盆把生豆浆倒进锅里,烧火的人往灶头里续了些柴禾,拉起风箱,大火烧了起来。很快,豆浆就烧开了。这时,火势也小下来了。又少许熬了一会儿,掌勺师傅把沫往外撇了撇,嘴里一边自言自语“点豆腐喽”,一边顺手端起灶台上一个盛着“盐卤”的碗,开始往锅里慢慢地倒,我仔细观察才发现,这只碗的上沿有个三角形的豁口,“盐卤”顺着豁口流下来,流得很细、很均匀。掌勺师傅一边往锅里倒,一边搅动着锅里的豆浆,慢慢地,豆浆开始凝固了,看上去像是一朵朵棉絮密密麻麻泡在汤里。又过了一会儿,师傅说:“好了,可以装盒了。”这时师傅注意到了我,就回过头去对着和我们一起磨豆浆的那人说:“快去拿个碗来,叫小子尝尝热豆腐脑。”不大一会儿,他们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递给了我,还找了个干净的小勺给我。看来,豆腐坊里经常会有人吃这一口,碗和小勺是常备着的。到现在我还记得,那碗豆腐脑真香,也真甜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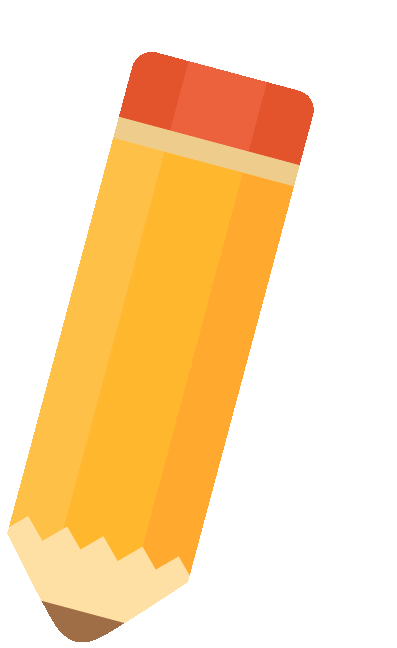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我婉拒了二姨家留我吃饭的诚心,推着做好的豆腐回到家里时,已过了中午吃饭时间。看到做好的豆腐,母亲免不了夸我一番。
有了这些豆腐,那年过年,我家炸的豆腐泡和豆腐丸子,蒸的豆腐渣窝窝头,还做了白菜粉条炖豆腐。
后来回想起那个春节,我把它戏称为过了一个“豆腐年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