美文丨枣儿红了 | 德州云-德州晚报全媒体
作者 春仲
那个秋高气爽的季节,我又一次来到了乐陵那片声名远播的枣林景区。
首先进入了“百枣园”。这是一个集各类品种之大全的特色园区,据说占地180多亩,种植着596个不同品种的枣,是国家级的枣树种质资源库。此时,累累硕果挂满枝头,它们大小不同、形态各异。小的如同指肚,像红宝石一串串挂满枝头;大的圆润肥厚,如贵妇人一个个尽显雍容。有的好像磨盘,有的状如辣椒,有的形似茶壶。早熟的已全身透红,红得发紫;晚熟的也已经泛红,略带青黄。进入百枣园,免不了采摘品尝,有的果肉紧实,甘甜如蜜;有的入口清脆,甜中带酸。百枣园里游人如织,和我们一样,大家都是一边欣赏美景,一边采摘品尝。
不知不觉,我们走上了为方便观光而修建的林海天桥。如果说在百枣园里看到的是品种之多,而漫步在天桥上看到的则是枣林之大。一望无边的枣林墨绿如海,阳光照射在叶片上泛起点点银光。天桥周边的枣树上,目之所及,即将收获的果实在绿叶的掩映中透着成熟的红,红得丰腴饱满,红得熠熠生辉,和湛蓝天空、悠悠白云相映成趣,正如有诗所云:“千家小枣射云红”。
枣儿红了,我的心也被它陶醉了,突然想起了老家的那两棵红枣树,想起了儿时有关红枣和枣树的那些往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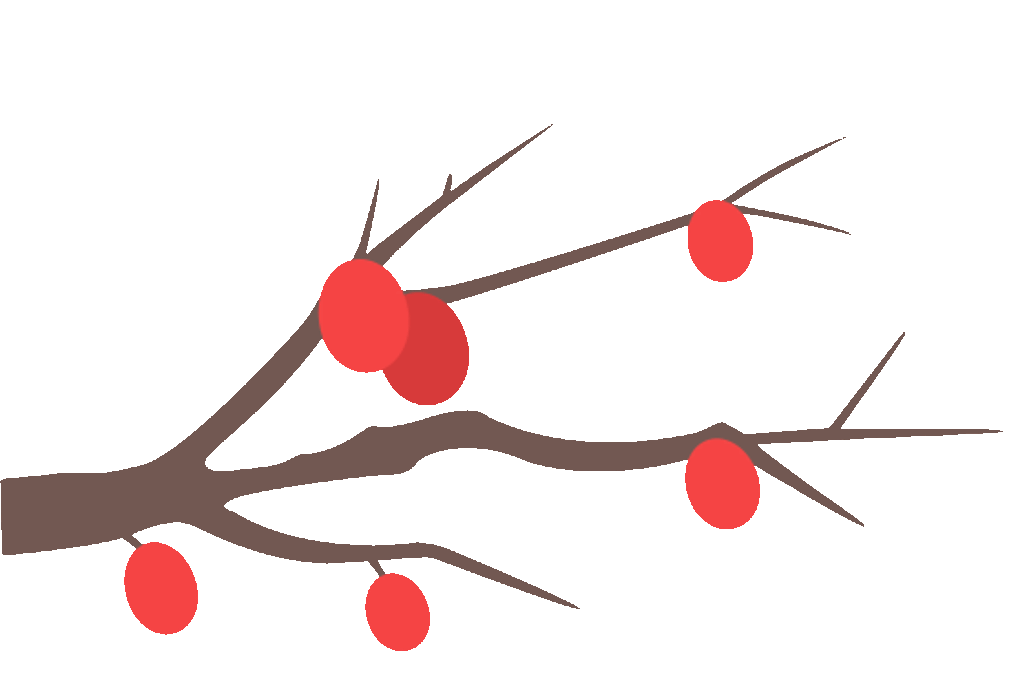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,老家院子的最前面种着两棵枣树,紧靠前邻的房子,从我记事起这两棵枣树就生长在那里,据说是父母结婚后种下的。两棵枣树一东一西,相隔四五米的样子,树头交织在一起,像一对不离不弃的恩爱夫妻,耳鬓厮磨,彼此依靠,相扶相持。树身不高,树头刚刚越过前面的房顶。从枣的品相和口感看,应该和乐陵小枣同属一个品种。吃鲜枣感觉肉质紧实,甜度很大,晾干了掰开果肉也会带出长长的金丝,吃起来觉得比鲜食更甜。
当时老家的院子里还种着杏树、石榴等果树,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两棵红枣树——不仅因为它能在收获的季节带给我们甜蜜的享受,更是因为它给儿时的我们带来了攀爬的乐趣。每到小枣开始发红的季节,我几乎每天都要爬上爬下好多次,挑拣即将成熟的枣吃。正如唐代大诗人杜甫所描述的“庭前八月梨枣熟,一日上树能千回”。凡是能攀爬到的地方,没等小枣完全熟透就都被我们采摘完了。每年这种时光有一个多月的时间,到了中秋节前后,树上的小枣就基本都成熟了。俗话说,“七月十五拣枣吃,八月十五打枣吃”。季节一到,就要选择个天气晴好的日子开始打枣了。这时我也会拿起竹竿,攀爬到树上或是前邻的屋顶上,和大人一起把树上的小枣打个干干净净,同时,也会借此机会痛痛快快吃下这一年中最后一次鲜枣。剩下的小枣就会晾干后保存起来,留待过年时蒸枣糕或者做红枣黄面窝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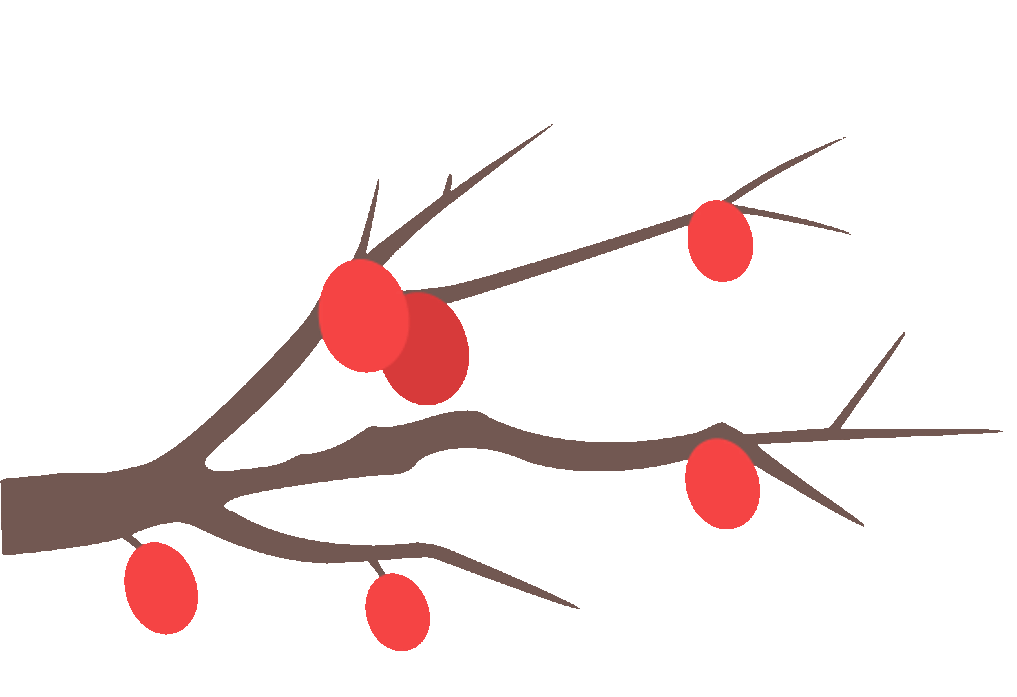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家前邻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池塘,人们称之为“大湾”。湾边上也种了十几棵枣树,没有和我们家小枣是一样味道的。有小巧玲珑、甜中带酸的“铃枣”,有个大肉厚、质硬味甜的“紫枣”,有口感松软、甜度略低的“婆枣”。我最爱吃的是“铃枣”,脆生酸甜,令人口舌生津。但好吃却不好摘,枣树长在湾边的斜坡上,树干细长,难以攀爬,站在坡上又够不到树枝,只能望“枣”兴叹。如果赶上大湾里水多,这就给我们采摘带来了便利——我们可以划着小船过去,站在船上,伸手把树枝拉下来。记得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,那两年雨水特别大,雨季过后,大湾里常常涨满了水,直到小枣成熟的季节还非常“充沛”。有一天中午,我和一个小伙伴,见湾边停靠着一个小船,我们便划着小船去对岸摘枣吃。尽兴之后,那个小伙伴便撑着篙划起小船准备返回,没走出多远,突然听到“扑通”一声,抬头一看,小伙伴落水了。原来那个船篙的底端插在泥中拔不出来了,小船靠着惯性还在前行,小伙伴忘了松开手中的篙,结果就被带到了水里。那时我刚刚学会游泳,那个小伙伴还不会游泳,我见状立即跳下水,想把他拖到船边,但我没能拖动他,却被他用双臂死死搂住了脖子。幸好我的二哥和另外一个邻居正路过岸边,及时把我们救了上来。到后来长大懂事之后,回想那次经历,我经常调侃说那是“一次甜蜜的代价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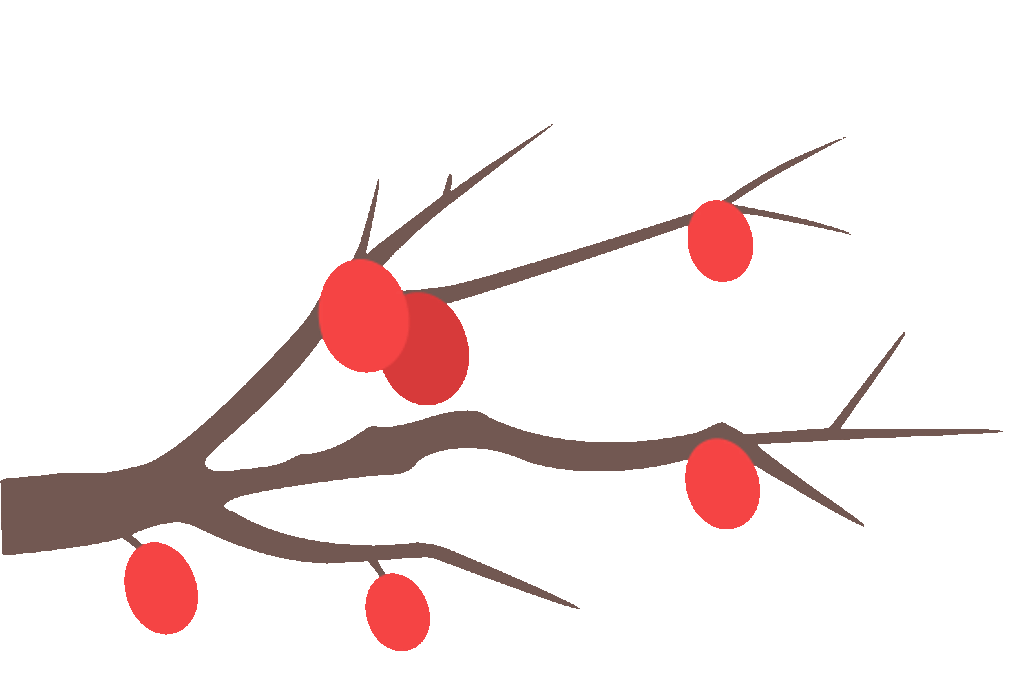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,老家院子里和池塘边的枣树早已不知所终,抚今追昔之间,冥冥之中,我感到它们好像早已融入了眼前这片令人着迷的枣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