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老德州杯”“我和我的祖国”征文丨张丽:青灯之恋 | 德州云-德州晚报全媒体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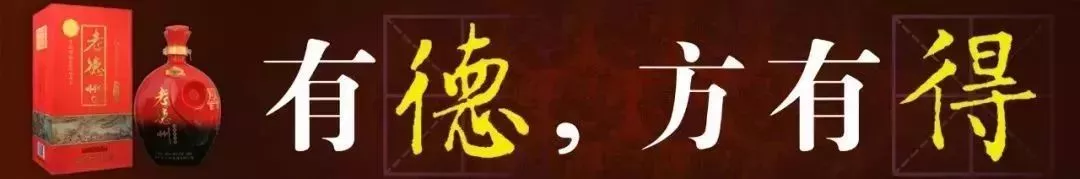
周末陪父母回老家收拾东西,在西屋角落里,我发现了它。30公分高,托着3颗“牙齿”,已经被厚厚的尘土掩埋了颜色。“泡子灯”,尘埃中,我似乎又看到它发出明亮的光束,灯下是我苦读的身影。
煤油灯岁月
我出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。当我懂事时就羡慕、敬佩当小学老师的母亲,在如豆的油灯下伏案备课。那时她是多么年轻啊!头发乌黑,眼睛明亮,昏暗的灯光下,母亲还没有皱纹。有时我一觉醒来,能看到母亲或是托腮沉思,或是“刷刷”写字备课,或是紧锁眉头,或是微微颔首。有时也会被缝纫机“咣咣”的声音惊醒,母亲借着油灯微弱的光,在给我和两个妹妹做衣服。那时母亲还是民办教师,工资少得可怜。我姐妹三个是“挨接”,我比大妹大一岁,大妹比小妹大一岁。母亲衣服改小给我穿,我穿小了的两个妹妹再穿。
慢慢的我上学读书了。晚上也会在油灯下学习。记得寒冷的冬夜,小屋里一个小炉子取暖,朦胧的灯光下,母亲给姐妹仨讲故事。印象最深的是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,灯光摇曳不停,发出噼啪的响声,听见母亲柔和声音的陈述和二妹轻轻的啜泣。三个女孩紧紧依偎着母亲,觉得很幸福很温暖。
姐妹仨都要写作业时,一盏油灯会显得很勉强,会被三只小手推来拽去,都想油灯离自己近点。小妹总是很霸道地把灯端到她眼前,母亲就会笑着嗔怪:“傻孩子,离你越近你会越看不见,不知道灯下黑吗?”也就在那时,我粗浅的理解什么叫“灯下黑”。第二天早上起来,母亲就笑话姐妹三个的小鼻孔像一个个小黑烟囱,催着我们赶紧去洗洗。
父亲变出泡子灯
有一天晚上,父亲端来一个两层像“塔”的瓶子,用火柴点燃粗粗的芯,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两头透气像葫芦的玻璃玩意,扣在瓶子上面。奇迹出现了,屋里顿时亮堂起来。姐妹三个叽叽喳喳询问着,父亲说:“这叫泡子灯,很亮吧。不要用手摸,会很烫”。有了泡子灯以后,我会陪母亲挑灯夜战。
多数情况下,母亲或批改作业或备课或者做点针线活,我看向同学借的小人书。泡子灯旁边有个小螺旋,可以调节灯光的明暗。时间长了,灯芯上会有一节儿灯花,母亲先把灯调暗,拿块桌布垫着取下泡子,飞快地用剪刀剪掉灯花,再扣上泡子,我感觉灯光会亮很多。
夏天的晚上,灯周围很快聚集一圈小飞虫的尸体,有黄绿色带透明翅膀的,有黑色、白色、黄色的叫不上名字的小虫子。有时还会飞来一只大蛾子,撞的泡子“当当”响。蛾子却不辞辛苦,撞了一次,又一次,直到跌落在灯下,微微喘息。母亲告诉我飞蛾扑火的勇气。我幼小的心灵会为之一颤。第二天悄悄把“蛾英雄”埋葬在院里,很神圣的三鞠躬,我做这些母亲不知道,她也可能装作没看见。
泡子灯虽然比一般的煤油灯亮,但是每天要清洗泡子,这项高难度的活,被父亲承包了。他总是选择在每天傍晚清洗。左手熟练的取下泡子,右手拿一块柔软的小花布,先往泡子里吐几口唾沫,小花布伸进去,一圈一圈慢慢擦拭。不一会儿,泡子被擦得光洁如新。也有被擦破的时候,父亲会无奈地摇摇头说:“劲儿用大了,再换个新的吧!”
就这样,我们每天在亮亮堂堂的灯光下学习,再也不用担心鼻孔变黑了。
泡子灯戴上“帽子”
和我同岁且从小一块儿玩大的堂叔的女儿叫扣。堂叔比母亲早几年考取师范学校进修,那时已经是一名公办教师。工资是母亲的7、8倍。堂叔又是个心灵手巧的人,用现在的话讲是“暖男”。他会理发,会做衣服,给扣理的发型十分潮流。我爱去扣家玩,有时故意赶饭时去。因为扣家的伙食好,扣的母亲做的馒头又大又白,赶巧了还能分到一块扣吃不了的鸡蛋。不知她是真吃不了还是想让我吃一块?我俩无话不谈,我告诉她,奶奶会把鸡蛋存在红木匣里,积攒多了就去集上卖掉。而扣的母亲不卖,会把鸡蛋都给扣和扣的弟弟煮着吃。长大以后,我还会对奶奶说:“我没扣吃的鸡蛋多,所以我长得比她矮,我要是能吃鸡蛋,没准能超过她!”奶奶总是笑而不答,会拿手绢擦擦眼角。
一天晚上,我去问扣作业,发现了“新大陆”。扣家的泡子灯上顶着一截用白纸卷成的直筒,她家的灯光好像比我家亮一些。回家后,我自己动手卷了个筒扣到泡子上,灯光非常亮。可是一会儿,纸筒开始蜷曲变黄变焦。母亲告诉我用的纸太薄。那时我们的作业本都是买大张的粉连纸,自己裁成合适大小的纸张,用线缝起来做成本子。仔细的还会打上横线或者画上方格。粉连纸因厚薄之分,价格也有贵贱之别。我央求母亲买张厚纸,小心裁成约16开大小,每天晚上给泡子灯戴顶帽子,享受明亮的灯光。
迎来电灯时代
80年代末,村里运来了许多根高大的水泥杆,大人说是电线杆,村里要通电了。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,天天数着指头盼着通电,用上城里人才能用的电灯。村东头盖起一间不很高也不算宽敞的砖房,很快里面安装满了设备。村里人都叫那间房“变电楼子”。好多年我家的那块地因为靠着变电楼子就叫“变电楼子地”,还有一块叫“电线杆子地”,因为一根电线杆就竖在我家地里。不久村里扯上了高压线,高高的线杆上顶着几根永远望不到头的电线。风一吹,电线就会发出“嗡嗡”的声音,一个女同学说电线杆会唱歌,并写进了作文里,被语文老师表扬了半学期,说她善于观察生活。
开始用上电灯后,电压不稳,晚上一写作业就停电,该睡觉时却来电了,村里人拉呱时,管这电叫“照光腚”。都说是城里人用剩下的电再供给农村。再后来,晚上来电了,却一会来一会灭,母亲赶紧让关掉,说会鼓了灯泡。
去变电楼子经过我家门口,停电不会超过十分钟,我能听到村里电工骑着“吱吱呦呦”作响的自行车,吹着口哨经过,他是去电楼子合闸。变电楼子在村东,电工家住村西头,我想电工最好住在变电楼里。小时候十分羡慕当电工。觉得他穿上那双大铁鞋,腰里扣上安全带,头戴安全帽,一步步爬上高大的电线杆检查线路,头顶着蓝天,多威风啊!记得那年四叔结婚,前天晚上“候戚”(读音houqie)。父亲担心敬酒时突然停电,就备下好酒好肉,听说是让电工在变电楼子里吃着喝着,随时准备应对停电。
不知道哪一天开始,为了应对停电,母亲准备了蜡烛。有时是红的,有时是白的。跳动的烛火,像多愁善感的邻家女孩,流泪诉说着爱情故事。那时流行学生给老师送明信片,上面都会写着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。刚流下的蜡油很软还有点温度时,可以随便捏成好玩的小东西,很像现在孩子玩的橡皮泥。不知道蜡烛制作时为什么后头会多留一截芯,这样我能在蜡烛快烧完时,迅速的把软蜡油子捏到一起,放进一截芯,做成小蜡烛,以备临时之需。
后来我离开家去外地上学,后又参加工作。村里经过三次线改后,原来的变电楼子、电线杆都废止不用,取而代之的是更高更粗壮的线杆。蜡烛渐渐淡出我的视野,前面冠以“生日”两字,成了过生日时才会记起的专用蜡烛。
总以为岁月无情,荏苒几十年,会用尘土封存我的记忆。如今是这枚“青灯”又让我走进遥远的过往。忆起那些年的人,那时的事,那会儿的岁月。